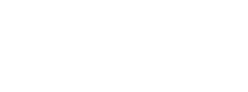大家放下報復 柯文哲也應投身司法改革(吳統雄)
作者:吳統雄(台灣民調創始人)
「25:0」台灣民意已明確決議:台灣必須放棄撕裂仇恨,所有為大罷免舖路的大逮捕,包括:證據不明、充滿程序瑕疵的柯文哲、最高本刑僅2~5的20餘位人民,以及被綁赴「823戰場」的各方人士,都應該解放桎梏,讓台灣回歸自由與團結了!
放下撕裂仇恨,必須由政權與人民雙方同時誠意進行。賴清德已宣示投入國家總資源,誓師823 血戰,可寄望性微乎其微。只能期待王世堅等真正「愛黨愛台」者的努力。同時,期盼司法圈中可能還有51% 以上具備司法獨立認知的人,能夠遠離隨附政治的利益。
人民方,柯文哲如果能夠出來,他是最有資格喊報復的人,但我將勸柯文哲將自身遭遇,轉化為制度改革的動能,使程序不義與比例失衡的借題迫害不再重演於任何黨派身上,朝向甘地式愛與和平、曼德拉式憲政修復之路。
我曾給過柯文哲2次建議,第一次是2014年我建議他以無黨籍身分參選,可贏15%,果然如是。第二次,是總統選舉藍白合作的截止日2023年11月22日,經由民眾黨依賴之智庫祕書長蘇進強推薦,正式邀請我擔任最後協商的民調專家,唯旋即放棄。如果是我擔任協商者,當前台灣的局勢一定完全不一樣!且台美陸的雙兩岸關係也可能極大不同。
有幾位地位崇隆的政治人士,在我們不熟悉、甚至不認識的情況下,第一次接觸,就是他本人直接打電話給我,包括:蘇貞昌、呂秀蓮、張善政、柯文哲。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,我們除了討論問題之外,沒有其他關係。我今天第一次說出來,是因為我的建言有一定門檻,會打電話給我的人,是本身有思考複雜問題的興趣,有必須科學解決的認知,以及有耐心讀完我科普的簡介,這些是證明他們具有「使命感」而不僅是爭取權力的特質。
柯文哲一度邀請我做藍白合作的終局協商專家,我的建議已事前多次公開報告:以各家民調「統合分析」的數字決,且不需要、也不應該談什麼「讓幾趴」,事實也證明「統合分析」和後來的選舉結果相同。
這個過程印證了人類的自然現象,我們心中都有2個意志,中外古今有不同的名稱:天擇(利己)論與親擇(利他)論、控制慾與使命感,最簡單的就是惡性與善性。柯文哲在經歷這麼大的磨難與迫害後,一定激起他更大的意志,有待他以哪一種意志來參考我的建言。
我將建議柯文哲獻身政法改革,不一定需要擔任政府領導人才能做到,正如許多宗教的創始人,均未擔任政治職務,而是以他們受難的經驗,與仍然慈悲為懷的堅守,而感召了信徒與人民。
當前第一要務就是「司法改革」,根據千百年的經驗與數量歷史學,適合出發的途徑有2條:第一、自律優先。第二、增強司法制衡功能。
「司法改革」在黃世銘的領導下,曾經出現一線契機,他一生在司法圈中認真服務,所以知道改革的第一要務就是「正己專案」,也就是自律優先,一度使公正的火炬大亮,正義的天平回正。唯在柯建銘結合廣大利益集團圍攻,發起與柯文哲案相同的「借題迫害」,以致功虧一簣。黃總長的目標不能改變,但他失敗的原因,必須集思廣益研究,以追求更落實的方法。
像土耳其的類強人體制,以選舉結果改變司法人事,是絕對阻礙國家向正常憲政發展的。
台灣司法制衡薄弱,依司法演化史與國際司法比較學説來話長。簡約歸納就是《法官法》實為《怠墮法官保護法》,司法職務等同「人要變神」,能力品德敬業條件極高,唯人本性好逸惡勞,對不適任司法人員保護過於周密,使追求富貴者,有違法弄權的機會。過去1年解嚴後的全國大逮捕,多名檢察官、後來又加上法官,屢屢明顯違背普世司法程序正義,反而步步高升,是台灣史上司法敗壞最嚴重的時刻!
我在擔任法扶期間,發現素質最高的竟是地方法院!素質也不過就是遵守司法基本準則與嚴格證據法則而已。證明年輕人投入司法領域,開始也多抱有維護正義的理想。但入行後發現權力太大,更可以交換榮華富貴,而愈高升愈容易(不是全部人員)扭曲。
所以加強司法制衡,也是在保護那些不忘初心的司法人員,減少那些鑽營者必然造成的升遷堵塞、干擾與臭名,能夠在較獨立的環境中為人民保障公平正義。
台灣應參照美、日、德、法、韓、瑞士及北歐諸國…等民主國家之司法制度,建立分級任期與評議退場機制,以提升司法透明與責任性。
當前有評議機制,但彭文正不久前在節目中揭露,他在擔任「檢察官評鑑」委員期間,發現除了他之外,根本沒有其他委員去過調閱室研究過事實資料。亦即「評鑑委員會」主要是聘請「護航委員」而不是「評鑑委員」。
彭文正的評論是否有事實支撐?我調查分析了2個委員會的報告。
「評鑑委員會」依新制應於2020年起,定期公布評鑑集計報告。
「檢察官評鑑」資料範圍自2020年7月17日至2025年1月31日,總收案數為969件,成立案數10件,年度平均不當案件 0.23%。而不當檢察官有8人,比較全體檢察官人數,年度平均不當檢察官 0.15%人。
「法官評鑑」資料範圍自2020年7月17日,至統計截止日:2025年6月30日,總收案數為800件,成立案數10件,年度平均不當案件1.25%。而不當法官有3人,比較全體法官人數,年度平均不當法官 0.03%人。以上只是評鑑成立,對當事人沒有任何懲戒作用。
如果以上數字為真,台灣真是全世界最公平正義的國家!
是嗎?
以最近律師主張的事實觀察,朱亞虎案,檢察官一再疲勞反復誘導,加威脅語意,將時間關聯久遠,210萬與行情差距更遠的政治獻金,逼迫朱亞虎為保命而亂咬的賄款。
沈慶京住院期間,檢察官私自前往詢問,也不錄音報告,到底私下說了什麼?
我在擔任民間法扶時,扶助的是小到公辦法扶不能接的小案,當事的是你根本不會知道的弱勢,高比例的檢察官,更是以人際關係辦案,如果恰巧對造是權貴,一定犧牲弱勢,結緣權貴。
據律師主張,以上是檢察官公然違背基本程序正義的事實,對照以上「台灣是正義天堂」的官方宣導數字,是諷刺嗎!
這種正常人都知道的事,我為何要加上「律師主張」?表示在此芝麻理由就可以逮捕押人的恐怖氣氛下,我只能以我的法扶知識自保,自認我是笨蛋看不懂,都是引述律師說。
我建議的改革基於「防禦性善意」,我們知道人類同時存在惡性與善性,不能幻想沒有惡人存在,同時,也要自我抑制惡意的爆發。所以設計的制度,不僅要預防綠營干涉司法,若藍白有機會執政,也必須預防藍白干涉司法。
正如行車的重要觀念「防禦性駕駛」,不僅要避免撞人,也要避免被撞。在制度上防止各黨派的司機,不因為彼此私怨而互撞,要把全國不同顏色公車中的人民,安全的帶到目的地。
我們更要呼籲在賴政權下,攀附政治利益的幾位司法人員,及時調整。台灣究竟已不是帝制,也不是強人政治,為鞏固一人的權力而犧牲公平正義,並無永遠的獲利。
黃國昌揭發民進黨高層關說大量司法人事案,如果屬實,不僅是對整體司法士氣的打擊,更是對司法獨立的自宮。
我們強調「以司法獨立為目標的改革」,但如果錦衣衛殺戮太重,會激起人民自發性、無法阻擋的復仇式改革,台灣千萬不能朝那個方向試探。
我建議柯文哲推動的政治改革,相對於司法改革基於歷史經驗,則具備創新意義。
第一個是「公辦初選」,同時可改善「不分區」名額分配的依據,選舉日不再發政黨票,提升選舉的效率。以及檢討對候選人個人競選經費之補助,興利之外同時革除數項弊端。
第二個開創性的政治改革,是我從柯文哲身上觀察與學習到的議題:「素人政治家的育苗制度」。
上世紀末以來,各民主國家,尤其是大都市,紛紛出現選出「素人首長」,顯示「53237選民結構」中的可改變選民,已不再跟隨傳統兩端意識型態選擇,其數量也足夠選出地方首長。
我兩次聽柯文哲簡報,在沒有人問的情境下,自己陳述在上任之初,所做的錯誤決策。我認識的政治人物中主動自省檢討的,極為罕見,人孰無過,重要是不二過,是我持續向他建言的原因。
各國的素人首長,後來出問題的相當多,反映素人雖然清新,但易缺乏必要經驗。正如水稻要茁壯,必須先育苗。
政黨有差異,國家須存續。故可開創「見習與輔導」期,新當選首長,在當選後、上任前,可先攜帶2位左右機要,進入政府見習政務,可發問,但沒有投票權。卸任首長,得應新首長之請,配合2位左右政務人員,擔任最多半年的留任顧問,協助說明一些承續計畫的細節,有被問義務而沒有投票權。
這在各國政府中未見,但在許多民間社團中,已經成為可以永續的核心因素之一。台灣如果率先啟動,不僅可改善政治文化,也為國際政治制度建立新標竿。
2014年,不參加選舉之第三方人員,請我對當年選情作個「隨機/等機率級」的調查預測,該委託案未含保密條款,故可公開。柯文哲的競選總管X先生(柯文哲書中唯一承認朋友的哥哥)是我文青時代的老友,在私訊中和我討論競選民調,我誠實告之:有一史上不曾發生的現象,在權衡加減抵消所有意識型態選民後,多出現有過去投藍、數量為7.5%者,可能改投柯,因為是「倒戈現象」要乘2,如果柯能夠「保持沒有顏色」,即可吸引這些人,會以15%勝出。後來選舉結果,果然柯以15%勝出。
X先生後來發文:他對柯文哲最大的貢獻,就是阻止柯文哲加入民進黨,因為當時柯文哲曾經考慮過入黨。我和柯文哲第一次見面,他馬上知道我是誰,更曾多次找不同幕僚來訪問我民調議題,顯示X先生有說明是我的建議。
當時我有同學任職中央,基於平衡原則,此事我也告知同學,同學也轉達給連勝文,連總部也派 2 核心人士來開會討論,我並就「勝選6策」提出建言,然後無下文。同樣一個數字,柯團隊作了因應,連團隊沒有反應,應該也是造成選舉結果差異的成因之一。
2023年11月22日是藍白合作協商截止日,前夕21日晚蘇進強通知我,柯文哲決定請我擔任最後協商方案的民調專家,上午在記者會中宣布,下午與藍團隊會商決議。
不久後,民眾黨發言人陳智菡果然打電話通知我,柯文哲請我出席22日的記者會。唯過了幾小時後,陳智菡又打電話給我,通知取消了。
我建議的決策方案曾與蘇進強數度討論,也在本專欄中公布:第一、將各家民調以「統合分析」判定高下。第二、不必讓3%。以上過程,我在發稿前已請蘇進強、陳智菡過目本文全文確認。
我為何建議「不必讓」,因為「白」是「可變群」與藍綠選擇以意識型態為主不同,而是理性抉擇。
許多人以為柯文哲的群眾是年輕人,因為廣場上看到的多是年輕人,同時坊間民調的「加權扭曲」,把實質沒有那麽熱衷選舉的年輕人過於擴張。我在2014、2018 對他的研究,發現柯文哲的支持中堅,實為必須扛著台灣前進,沒有時間上街頭的知識分子,可以蘇進強為範例。
「白」的群眾並不能接受領袖密室協商,然後把自己呼來喚去。蘇進強當過台聯主席,故為全局著想,因為支持人民、支持國家、而支持柯文哲。
基於「統合分析」柯文哲就是排第三,即使柯文哲願意接受事實而退居副手,他和侯友宜一加一也會小於二,他必須誠於本心—而不是別人要求他—誠懇向群眾說明,合作才是人民與國家和平繁榮的道路,才有可能達成團結。
選後,「統合分析」的預測果然和選舉結果一樣,同時,還可以觀察出有2家民調存在無意或故意的錯誤。詳細報告在:《看懂民調:總統大選民調總檢討 權威學者一一檢驗!》。
張良之所以是張良,不是因為自己,而是因為劉備。張良和蘇進強一樣,什麼也不要,只要台灣前進、全民幸福。
柯文哲並非無錯誤,必需負責承擔。但身為「借題迫害、不成比例」的受害人,被壓迫的力量一定會爆發反彈,我建議他不必反彈報復,而反彈為司法改革、政治改革,建立保障全民的機制,將自己的苦難升華為消弭未來任何人不再被迫受難。
*作者為「新故鄉智庫」國政顧問,本文原刊於114/8/3中時,由作者授權轉載。